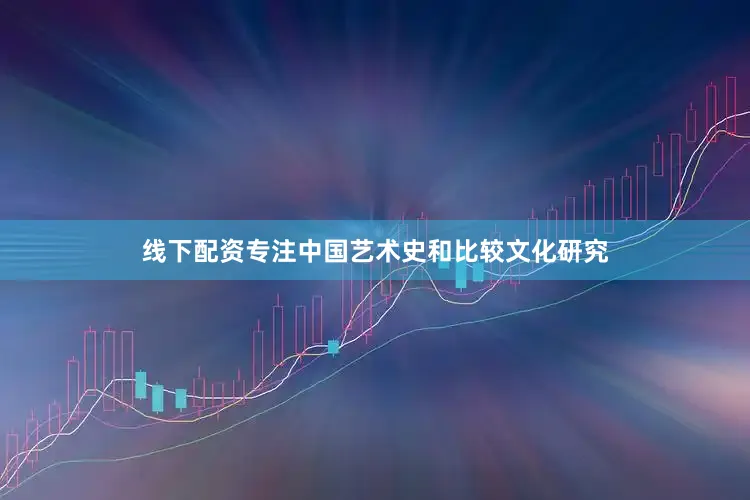
《刺客聂隐娘》
从书画、礼器到园林、建筑,中国艺术自古便展现出一种蓬勃的生命力。我们欣赏中国艺术,远不只是欣赏其表象的精美或壮阔,或者说,把握每一种艺术背后携带着的时代印记、蕴藏着的文化与历史渊源,才能让我们真正感受一座园林的美、一幅书画的力量。
在《如何打开中国艺术》中,25位来自北大、复旦、牛津、斯坦福等名校的一线艺术史学者将为我们打开了解中国艺术的全新视角,巫鸿、白谦慎、杨晓能、伊沛霞、杰西卡·罗森、文以诚、卜寿珊等25位艺术史大家在书中各以一章篇幅, 全面梳理了中国艺术25个面向的基本问题。
以比较文化的视角重新打开中国艺术,以“事实的药方”打破中心主义、本位思想等“古老的成见”,是我们真正走进中国艺术的第一步。
展开剩余90%主编包华石是艺术史研究大家,专注中国艺术史和比较文化研究,曾获列文森奖,是密歇根大学艺术史系荣衔教授,自 2022年起在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任教。
书籍采用 全彩插图,并新增 20幅高清文物配图,以 雅质纸印刷,采用 32开精装打造小开本,重磅、美观、耐看。
作为理想国“大家的艺术史丛书”的最新一册,本书既是适合多数人的中国艺术史进阶读物,也能让我们在丰盛的诗词书画中尽情感受古典艺术之美,领略中国文化的独有韵味。
包华石亲笔签名❗️
精彩好书,不要错过❗️
01
自10世纪以来,山水一直是在中国画史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画作主题,然而其根源可以上溯至1000多年前。根据定义,“山水”是指与人类的建造和活动截然不同的外在世界、山川和河流。我们可以假设画家描绘世界是因为对世界的现实感兴趣, 但这并不意味着画家的目标是对视觉感知的世界进行再创造。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富春山居图》的第二次展览,旨在将这幅黄公望绘制于14世纪的画作带入21世纪,吸引现代的观众,而其中那些写实的谬误之处显而易见。在这次展览中,主办方运用50台投影仪对《富春山居图》进行多媒体展示,借助计算机制图,数千张山水照片被巧妙地连接在一起,黄公望的“画作”被放大,投射在一面巨大的墙上,其构图由此得以如照片般神奇地展现出来。“现实”的《富春山居图》在视觉上引人入胜,尤其是当它与动画、声音效果相结合时,更是富有魅力,但它也令人感到不安,因为这种方式将黄公望的画作降格为一种简单的假设,即其主要功能或许只是传达黄公望在漫游时所看到的14世纪的风景。统览此后中国艺术中的山水主题,画家的关注点在于构成山水体验基础的“主体性”。画家作为主观的代理人,而非透明的媒介, 其重要性可以追溯至山水作为中国文化表达这一主题的肇创之始。
在东汉时期,人们看待和体验山水的方式开始发生重要变化。想象中的山水,带有异兽、充满未知危险且凡人不宜生存的山水,逐渐被驯化,被蕴含真实体验和审美欣赏之地的描绘所取代。在这种转变背后最重要且唯一因素或许是,归隐作为为国家效劳的一种代替性选择,在 2世纪日益流行。
在儒家和道家的哲学传统中,归隐都有重要意义。归隐可能意味着政治抗议、道德纯洁,或仅仅只是一种以“道”来摆脱世俗事务纠缠的愿望。在汉代,隐士作为模范人物拥有极高地位。无论是对于从社会中解脱的真实表达,还是带有看似“崇高”意图的虚假姿态,归隐通常意味着追求与自然韵律相一致的田园生活方式。 换而言之,归隐和山水是彼此相关的。汉朝覆亡之后,持续的政治动荡增强了归隐对人们的吸引力。在4世纪拓跋族征服了北方,晋室南迁到长江三角洲之后,这种情况尤为明显。
《刺客聂隐娘》
02
在汉代后的几个世纪里,山水的人性化对山水的描绘非常重要,尽管在当下看来,这种转变主要限于文本层面。诗歌是欣赏山水自然之美的主要表达载体。对画的评论则是另外一个重要来源,其中就包括宗炳和王维的那些直接将山水作为画作主题的文本,而前者的《画山水序》更为全面周到。
宗炳首先着眼于山水的精神本质,他通过关注包括传说中的黄帝、圣君尧、孔子以及各种模范隐士等在内的古代名人在山中寓居和漫游的方式, 切实阐明了山水的人文主义特点。我们了解到,这至少是宗炳在早年,即其自身精力集中和体格硬朗时期的一种强烈倾向。随着年龄增长,宗炳在卷轴和墙壁上描绘之前的漫游经历,从而可以 “卧游”。在这篇短文中,宗炳用部分篇幅讨论了一些必须引起格外关注的问题:艺术家可以将规模巨大的物体缩小到只有几寸,从而以二维形式捕捉山水的体验。早期的作画实践更侧重于单一对象,而不是将物体整合到一个延展的、逐渐远去的空间之中,因此描绘山水带来了显而易见的技术挑战,而且几乎无法为之提供准则。在山水画初创的历史阶段,描绘山水的可靠证据很少传世,但根据现存的情况而言,人们怀疑宗炳的“卧游”是借由画作中的视觉提示来唤起个人记忆。 画家需要花费一段时间,才能够掌握穿过群山沟壑进行如身临其境般视觉旅行的技术。
在11世纪宋代知识分子的观念中,此前两个世纪(即唐代末期和五代时期)大部分时间以国家秩序分裂和社会动荡为特点,这对彼时的文化成就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然而可能有人会说,山水画的情况恰恰相反。在唐朝的统治瓦解后,战争以及不稳定的社会状态促使人们转向自然,以求获得秩序和安定。此外,画家日渐增多的技法,也促进了对细节的观察和关注。因此对山水及相关鸟类、花卉和动物的自然描绘,能够实现如此惊人的生动感,以至于后来的观者认为这是一项非凡的成就。今人对这一时期山水画的相关看法,与早期的赞誉遥相呼应,都认为此时的山水画达到了古典的卓越标准。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纵观中国画漫长历史中的广阔背景,我们将10至11世纪的自然形象与逼真性相联系,这与其说是规则,似乎更像是例外。
《刺客聂隐娘》
在山水画的这一重要时期,留存下来的作品非常稀少,其中一幅带有“洪谷子”题字的落款,而这恰好是荆浩的号。与早期的山水画相比,《雪景山水图》以竖幅构图。位于图画中央的山脉是由带有人物的密集陡崖组成,山间有一座庙宇和一间位于前景的隐蔽小屋,整幅画面如同一条巨大且富有生气的蛇蜿蜒上行。据说此画是上世纪初在一处墓葬中发现的,画作今已残破不堪,并且与许多归于当时名家名下的作品一样,其创作年代也一直备受争议。然而,这幅山水画显示了一种在用墨方面新鲜有趣的实验方法,这尤其体现在画中很多石缝和沟壑中,这种表现与人们对唐宋之交绘画的希冀相一致。
03
在荆浩之后,许多画作都可以作为山水画的代表, 但没有一幅能够像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那样令人印象深刻。《溪山行旅图》在视觉、完成度和物质存在(高达 2米)等方面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其主旨和面貌具有无与伦比的表现力。首次观览之际,观者可能会感觉自己突然看到了一个壮观、瞬时的远景,并在一条向上延伸的道路上行进,而这条路与占据画面构图的巨大悬崖是平行的。 这种特殊或偶然的感觉,乃是范宽画作的特质,且有别于当时其他的山水画。
范宽《溪山行旅图》
《溪山行旅图》的构图布局与行进在路上的细小人物这一叙事细节相互结合,其中小路是从画面右下方的树林延伸出来的,因而使人们产生了那种随画作从右向左平行移动的感觉。虽然在画面上,两位乡下的商贾和四头满载包袱的驴子被画得很小,但是我们的目光却正好被位于其上方垂流如柱的瀑布所吸引,从而注视到他们身上。 我们能够预见到他们的运动,沿着略微向下倾斜的道路行至画面的左边,这反过来又得到了位于画面中部薄雾的微妙回应,以及背景中山峰急剧向下的拉力的着重强调。
与这种下落形成强烈对比的主要是中间的山峦,它以巧妙的透视法向上并向前突显出来。位于画作最底部的一系列反向的巨石,增强了主体山峦的中心效果。通过仔细观察,我们可以发现这幅画存在第三个人物形象:一个僧侣出现在上方岩石顶部的后面,朝位于画面下方中部的横跨溪流的栈桥左边走去。他走向右边,目的地是最右侧的寺庙建筑群。 这些稳定和平衡的综合效果,是一种偶然得之的完整感,也是一种自我克制,它使得《溪山行旅图》超越了偶然的初始印象,并使观众对更伟大的事物有所感知。
《溪山行旅图》标志着山水画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一方面,它实现了最早有关山水画 “方寸之间,气象万千”的期许。就像昆仑山一样,这是一个奇特的世界,但它源于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这 幅画作的现实感及其附带的暗示,使所有的幻想更加令人愉悦,但实际上乃是庄严崇高的。
《刺客聂隐娘》
04
显然,山水画是一种颇受文人青睐的画类。苏轼认为山水画 “无常形”而有“常理”,他借指那些尽管外形千变万化,但仍按照固有的自然规律出现的事物,因而要求在这类画中体现出更高层次的思想、理解和技巧。米芾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大抵牛马人物,一模便似,山水摹皆不成。山水心匠自得处高也。”按照宋代文人的表达习惯,“高”兼具道德高尚和质量上乘之意。他们在观念中很自然地将绘制的山水画与作画的人联系起来,因为他们明白,笔下的山水,无论怎样与现象世界相关联,仍主要是心灵的产物。这种意识肯定在之前就存在。11世纪的与众不同之处则在于强调人文主义的价值观,在将绘画理解为表达自我的工具方面尤为如此。这一点对观众的期待以及画家的动机产生了深远影响,它鼓励画家寻求方法,在所描绘的场景中留下个人的印记。
《刺客聂隐娘》
假设一个人足够富裕且拥有土地,那么最直接的完成方式就是绘制自己这片土地上的山水。例如,苏轼的年轻门客李公麟,以绘制了在龙眠山(位于安徽省)的自家庄园而闻名于世。李公麟用程式化且古意盎然的方式呈现了山水画的主题,画中格局纵横开阖,而且具有强烈的人的存在感。对于这种方式, 10与11世纪绘画的自然主义准则几乎无法辨认。重要的是,李公麟居住在距离龙眠山千里之外的京城时,首次创作了这幅作品,而现在只有摹本存世。我们认为李公麟的山水画是一种个人的象征, 它不仅意味着他的住所,而且还代表了他的博学、趣味及内在的美德,这是他在山中寓居的纯洁性的最好体现。
从根本上说,北宋文人以一种简单、直率的方式构思山水画——这恰恰与在京城做官带来的特权生活相悖。对李公麟而言,这就相当于家乡;而对他人而言,可能是被政治流放的残酷现实。苏轼就是如此,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陷于党争的旋涡之中。苏轼似乎没有尝试过绘制山水画,但是他的好友王诜这样做了。由于受到苏轼的牵连,王诜创作山水画以作为共同经历的象征,为共同的外放旅途留下痕迹。王诜的山水画以在艰苦且偏远地方的真实生活体验为基础,然而这些画作本身就是幻想, 他将山水美化成一个人们可以过着无忧无虑生活的地方,不用被那些主宰他和苏轼生活的野蛮政治现实所束缚。所以,虽然只是在友朋间的私下交流中分享放逐生活的痛苦,这种虚幻却以一种颇为奇异的方式表现了高度的真实。 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迹象能更好地表明:主观性在何等程度上融入了山水画艺术之中。
——摘自《山水画》·石慢
《刺客聂隐娘》
25位艺术史大家
全方位打开中国艺术
内含包华石亲笔签名❗️
精彩好书,不要错过❗️
🎁
发布于:北京市凯狮优配-加杠杆股票-炒股如何开杠杆-在线配资开户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炒股配资平台网址皇马客场4-1击败莱万特
- 下一篇:没有了



